明代江浦县驻军诸问题考述(下)
甘继民
【导读】
此文上篇讨论了明代江浦县驻军四个问题:(1)浦口城先后进驻“五卫”;(2)洪武年间建江淮卫于旷口山下,并迁县治与卫俱;(3)江淮卫管辖马快船,实为朝廷水上运输队;(4)浦口城“三仓”问题。下篇将讨论(5)县内营屯:屯营,屯田,草场等等;(6)军卫与地名;(7)举例简说“卫籍”士人籍贯认定问题;(8)如何处理军地矛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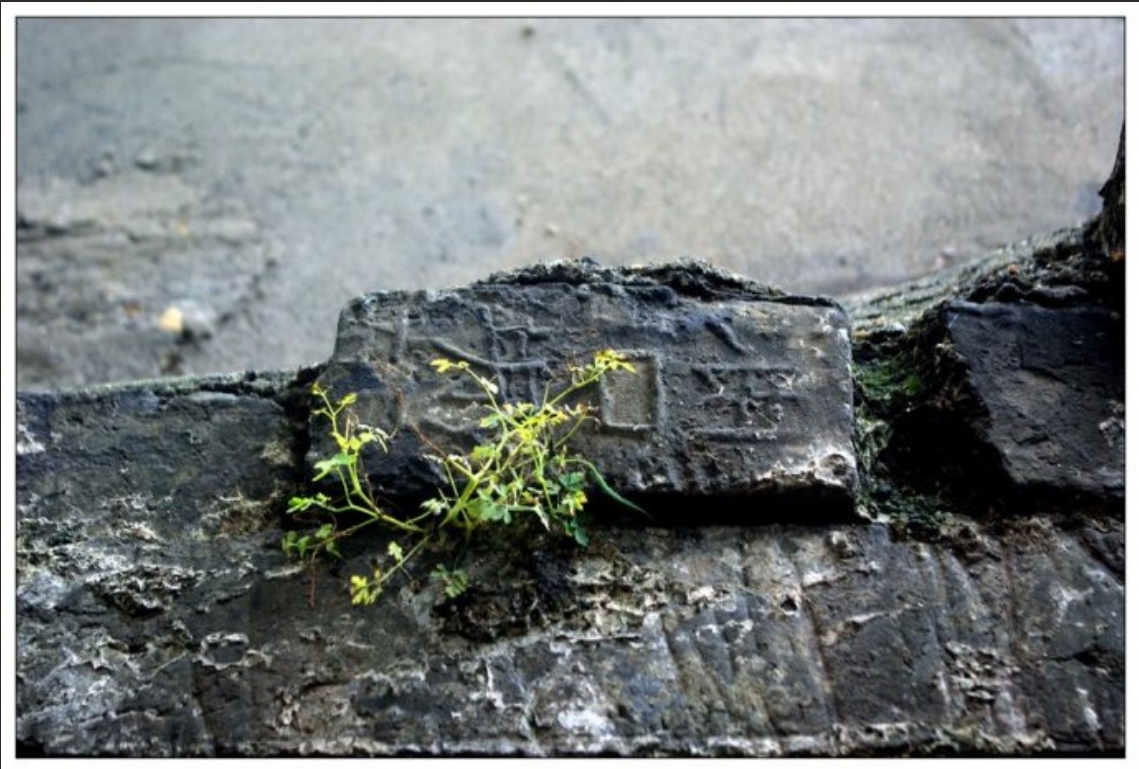
5.县内营屯:屯营,屯田,军营,草场,牧场,教场
明代的卫所制,采取的是兵农合一、屯守兼备的策略,战时是军人,平时是农民,战士们农闲时参加军训和演练,农忙时则参加田间劳作。这种兵制不但保障了兵源,也满足了军队的粮食供给。战士们集中住宿,其驻地叫做“屯营”。朝廷又动员和组织其妻子儿女前来同住,共同生活,屯营遂逐渐形成村落、里閈、集镇,若干年之后,许多军人子女遂入籍本地,以便就读县学,参加科举考试,或从事其他谋生行业。
江浦县域狭小而屯营较多,许多屯营杂处于当地村落之间,卫田与农田也难以划然分开,由此也带来很多矛盾(后文讨论)。
据《沈志》,县内有六处屯营:(1)锦衣卫屯田千户所:在遵教乡石碛桥(今属桥林街道);(2)镇南卫屯田中前所;(3)镇南卫屯田中后所:二所皆在县治西南二十五里白马乡(约在今江浦街道高旺社区);(4)和阳卫屯:杂于崇德、孝义等乡(在浦口城西门外,见前文);(5)旗手卫屯:在县任丰乡(今属汤泉街道,部分在星甸街道);(6)鹰扬卫屯:在遵教乡(今属桥林街道)。
此外,不同于屯营(营房及周围屯田,相对集中),各卫可能还另有散布各地的屯田(较为零散)。比如应天卫在今星甸、汤泉、北城圩、盘城一带滁河圩区,各有所属的屯田。
为监督管理军屯问题,南京都察院还曾在浦口城设“屯田察院”,作为监察御史过江来此办公、休息之用。
供战士驻扎和演练的军营,不同于“屯营”。据《江浦埤乘》,县内另有五处军营:(1)宁家营:在县城南三里。(2)白塔营:在治西三十里,今星甸一带。(3)善安营:在浦口城朝宗门外十里许,大约在今花旗营一带。“沈志”谓“以上三营,每岁正月初五日始,三月十五日止,操演各卫屯军”,可见明朝“营”兼有县内卫所驻扎、各卫屯军定期会操、供上司莅临阅兵的场地功能。(4)间山营:在浦口城后,大约在营盘山一带。(5)杏花营:在乌江。
洪武中县内多处建有牧马场,原设六处,后增五处。嘉靖十年(1531)始,因江北不宜养马,各处牧场“听民认垦、升科”(即任凭居民开垦为田地,只需报官定额缴税即可),遂逐渐改作普通农田。惟任丰乡(汤泉地区)仍保留锦衣卫、旗手卫等两处草场,其主要用途是训练骑兵,而非养马。
教场,又写做“校场”,又称之为演武场,是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。“沈志”仅记载“浦子口教场”一处,旧在浦子口城望京门外,后坍江淹没,弘治十二年,移至万峰门(西门)外三里六峰圩,每岁春秋操练应天等五卫官军于此。《江浦埤乘》则记载四处:一在县城东北里许;一在浦口万峰门外六峰圩,清代仍为驻兵操演之地,光绪年间废;一在浦口城内武德卫署附近,计十五亩,名射圃,晚清属“浦口营”,名东教场;一在府山前浦口营都司署西侧,晚清名之曰西教场。此外,同光年间,尚有吴长庆“庆字营”等浦口驻防军在浦口朝宗门内、攀龙门外、城隍庙西、江沿街南等处在居民区间开辟的“平作操场”(临时性的),不在此列。
6.军卫与地名
明代大量卫所军屯于此,产生许多地名,如今大多已经成为“历史地名”(不再使用,地名消失),也有许多至今仍在使用,只是地名来源和意义已经模糊,简述如下。
(1)仍在使用的地名
左所大街:在浦口城东门外,南接东门大街,北至碧泉,与朱家山河毗邻,长约一千米,明清建筑保存较多,今老建筑多已拆除。明代军卫下设“所”,一个建制完整的“卫”,下设左、右、前、后、中五个“所”。《雍正江浦县志》始出现“左所巷”,《江浦埤乘》出现“左所大街”。今缺少史料以确定“左所”所隶属之卫名。如前所述,明初应天卫驻鼓楼一带,和阳卫驻西门外,龙虎卫驻西门内,横海卫驻南便门(望京门)内,武德卫驻东门门内,此“左所”有可能隶属武德卫。当然,也可能是弘治年间驻扎在南门被水淹最严重的横海卫之“左所”,后迁至此地。
龙虎巷:在浦口城西门内,《江浦埤乘》谓浦口附凤门内有龙虎山,“下为龙虎巷,旧有关,额曰‘龙虎旧里’,即明龙虎卫所居”。晚清民初,津浦铁路通车前后,大量来自天津的技术人员入驻此巷,带来许多天津风格的住宅建筑留存至今。“龙虎山”显然也得名于龙虎卫。
(2)历史地名
江浦县城西南郊圩区(旧为沿江小圩,后合并,今属江浦街道),据《江浦埤乘》,旧有黄所圩、和阳圩、刘所圩、谢所圩、李所圩、欧所圩、教场圩等地名,上世纪五十年代后,犹有李所、沈所、谢所等地名,1958年由李所、沈所,谢所三个高级社联合组建生产大队,取名三合大队,1981年,又与河北大队,合并“四所村”,属江浦街道。“黄所”等地名,极可能源自江淮卫所属各“所”,黄姓或为该所最初“所长”(千户,或百户)姓氏。
旧江浦县地名里的“营”,可能大多与明代军卫无关。如朱家营(永宁街道),据“一普”走访调查,元末朱姓为躲避战乱,自安徽凤阳来此建村,村址曾扎过兵营,故名朱家营。郑家营(永宁街道),民国初期,郑姓从山东迁此,建村于清末兵营废址上,故名。周营(桥林街道),清末建村,村民多周姓,太平军曾在此扎营,故名。李营(桥林街道),位于周营西南2.5公里,太平军曾在此扎过营,后李姓建村定居。黑扎营(盘城街道),相传太平军曾黑夜到此,扎营过夜,故名。
(3)有几个特殊的今仍在使用的地名,需要略作研究
一是营盘山,在浦口城旸谷门(北门)外,定山南麓,今大顶山下,《江浦县志》未载此山,俗称此地为“老营盘”,又称营盘山。此地应为明代“间山营”所在。
一是花旗营,地名来历及含义迄今不明。此地名最早见于《江浦埤乘》卷一《乡保》,谓江浦县东乡有“花旗营保”,但未详地名含义。笔者推测明初该地为“善安营”,乃符合《江浦埤乘》卷十三《武备》所称“善安营:在浦口城朝宗门外十里许”的记载。今该地仍为军营(“舟桥旅”等军事单位用地)。《南京地名大全》等书称“传为清军浦口营八旗兵营地,故名”,有一定道理在。

(读书一生照片:江浦县城西门大街城隍庙巷地名牌)
7.举例简说“卫籍”士人籍贯认定问题
籍贯,《辞海》解释为“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”。这样的解释,用于明史研究,会产生许多问题。在明代,籍和贯并不是一回事,贯指“乡贯”,相当于《辞海》所说的籍贯;籍则是“户籍”,是世代承袭的对封建国家应负的不同义务,分别为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灶户(设灶煎盐)、渔户、船户等等,总计超过80种。户籍世代相承,严禁改籍。卫籍,即军户,是明代卫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户籍。
按一个满编卫5600人计算,明初浦口城“五卫”将士总数近三万人,若加上陆续迁来同居的将士家属,这个数字恐怕得翻上一倍。当然,永乐十八年起应天、龙虎、武德等三卫大部分将士陆续调往北京,留守浦口城将士及其家属估计仍有两三万之巨。驻县城的江淮卫大多为水军(水手),入驻县城的军人及其家属应有数千人。这六个“卫”之外,县域内还有来自南京锦衣卫、旗手卫、镇南卫、鹰扬卫等卫所的屯营,估计也有数千人。不论其原籍(乡贯)在哪里,这些将士及其子女都在江浦这个地方取得拥有一个新的户籍,这就是“卫籍”。
卫籍将士六十岁以后可以告老辞职,其子孙后裔须有一人承袭其军职(军官或士兵),军户里其余成丁(所谓余丁)作为“预备役”,可以暂时从事其他职业,当然,也可以读书科举,并登入仕途,从而脱离“卫籍”的责任。
为解决卫籍后代读书问题,明英宗朱祁镇诏令天下卫所皆设置“卫学”,学内也设教授、训导等职,生员称为“军生”,仍隶卫籍,但享受“民籍生”一样的科举考试待遇,一旦中举或成进士,则登入“仕籍”。若地方无卫学,则军生可入县、州、府儒学,当然也可入太学。查江浦县志,未见县内曾设置卫学的记载。属卫籍而成举人、成进士的江浦人不少,在表述他们的“籍贯”(哪里人)之时,措辞要分外小心。
下文例举明代江浦县卫籍里的著名人物,并兼及其籍贯表述等有关问题。
(1)王徽、王韦、王逢元
王徽(1428—1510),字尚文,号辣斋,天顺四年(1460)进士,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左参议,为成化、弘治间著名政治人物,其事迹见《明史·列传第六十八·王徽传》。关于王徽的籍贯问题,各家表述有点混乱。据储巏《王徽墓志铭》,其先祖为河南考城(今属开封市)人,元末徙家江浦,明初“隶”锦衣卫。锦衣卫设于洪武年初,永乐十八年(1420)跟随朱棣迁至北京,但江浦县怀德乡(今星甸街道一带)仍驻有锦衣卫屯营,因此《江浦埤乘》称王徽为“(江浦县)怀德乡人”;锦衣卫屯营直属南京亲军卫,《明史·王徽传》据此称之为“应天人”;查“明代进士登科录”,则记述为“南京锦衣卫籍,应天府学军生”,似乎与江浦县毫无关系,大概王徽中举、进士以前曾就读应天府学;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则记述王徽之子王韦的籍贯为“锦衣卫籍,江浦人”,这一记述最为合乎事实。王徽的籍贯也当如此表述。
王韦(1470—1525),字钦佩,号南原,弘治十八年(1505)进士,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(正四品),其诗婉丽多致,与顾璘、陈沂号“金陵三俊”。
王韦之子逢元,字子新,遵父嘱不应科举,而博及群籍,工诗。韦父子又俱善书法,时人以南原为右军(王羲之),子新为大令(王献之)。据说顾璘对王逢元甚为器重,其宅厅、书房各处皆悬挂王逢元书法与诗词。江浦有祖父孙三代人物风流如此,江浦县志编者当然大书特书之。特别是王韦,终身不曾中举解褐(脱去平民所穿的衣服)脱籍,始终为“锦衣卫籍,江浦人”。
(2)石淮
石淮(1442—1503),字宗海,天顺六年(1462)中乡试,成化二年(1466)成进士,改庶吉士,授户部主事,历四川、河南提学佥事。《江浦埤乘·石淮传》称其为“江浦县白马乡人”,其进士《登科录》则称为“贯应天府江浦县,军籍,国子生”。庄昶与石淮为同年进士,又有儿女亲家关系,石淮父亲石金死于成化十六年(1480),庄昶为作《石公墓碣铭》,称“其先温人”,不知是河南怀庆府温县人,还是指浙江温州府人,又何时迁居江浦,何时入为“军籍”,皆语焉不详。有关石淮的籍贯,最严谨的表述应当是:祖籍温人,先祖为军籍,驻白马乡,故为江浦县白马乡人。
(3)焦竑
焦竑(1540—1619),字弱侯,号澹园,二十五岁中举,五十岁时,得中万历十七年己丑科(1589)进士,殿试第一名(状元),任北京翰林院编修,因称焦太史,历官十年,辞职而去,自谓重作书生,七十岁时,被任命南京国子监司业(太学副校长),一年后辞去。隐居著作,有《澹园集》《国朝献徵录》《焦氏笔乘》等传世。
其祖籍为山东日照县花崖里。据有关史料,先祖焦朔(明太祖为改名焦庸)早年追随大将军徐达,作战英勇,屡立战功,后被编入朱元璋亲军,获得旗手卫副千户世职,守卫奉天门(南京皇宫正殿前门),后改派屯守江浦县任丰乡(今汤泉街道及星甸街道东)。今星甸街道万寿河左岸(西岸)有焦庄,地名孟泽山嘴,为其先祖所居之地,有祖墓在焉。今已荡然无存。
大约从焦竑之父后渠公这一代起,始从焦庄迁入金陵城,时在明朝正德、嘉靖之际。后渠公,名文杰(1503—1584),字世英,号后渠,三岁失怙恃,十六岁袭千户职,享年82岁。焦竑《与日照宗人书》云“德靖间,饥疫相仍,一门凋谢,只余吾父(飞)骑都尉一人耳”。查《明史·五行志·疾疫》,嘉靖二年七月,南京大疫,军民死者甚众;沈孟化《万历江浦县志》卷一记载,“(嘉靖)三年(1524)夏,大疫,死者相枕于道。”大约焦竑父亲正是在此二年“大疫”之后调往南京旗手卫,又十六年之后(嘉靖十九年,1540),焦竑出生,占籍应天府江宁县,故而《明史·列传第一百七十六·焦竑传》谓其为“江宁人”。
焦家既为卫籍,焦父死后,其千户一职得有儿子世袭,好在后渠公育有四子,焦竑行三;长兄焦瑞,先已以贡生身份“解褐”,任岭南灵山知县;遂由次兄焦靖袭千户职。再后承袭者不详,据《康熙重修江浦县新志》,明朝灭亡前,承袭者为焦竑之孙焦荫茂,字子常,清兵下江南,倒戈投降清廷,担任瓜洲参将,战后被裁,“遂退居江浦,庐祖墓侧,优游林泉”。
焦竑一生对焦庄念兹在兹,因此与江浦士人多有交往。据陈作霖《金陵通传》卷二十:“(焦竑)生平博极群书,为文典雅,以昌明圣学为己任,与江浦雷孟春、郑朝聘……相师友,四方同志者论道无虚日。”而他对故乡山东日照宗亲也不能忘怀,中进士后曾作《与日照宗人书》,情系桑梓,为宗庙购置田产,以供岁祀,并接济族人。焦竑墓地不详,应该不在焦庄。但直至清康熙年间,焦庄一直有焦氏族人居住。
(4)郑氏三兄弟
康熙间邑人进士刘岩称赞浦口城郑中先生:“吾乡固多奇士,然有道而文者,惟郑中先生为最。”郑中,字子绂,刘岩引之为“吾乡”,实际上其原籍为福建长乐,所谓龙台郑氏。曾祖国庸(其族谱名为“敬庸”),字起予,明季以太学生任职龙虎卫经历,遂家于浦口城。祖父纯守,字我爵,敦行善事,被举乡饮宾。父亲良翰,字用梅,多隐德。郑中兄弟三人,伯兄代绅,字子簪,仲兄选,字鹿萍。三人皆工诗,世称“郑氏三诗人”。曾祖在城南门外筑有一个别墅,名叫野园,园内有松柏数十株,老屋八九间。每当暇日,郑氏三兄弟吟哦其中,又艺花莳竹,邀客煮茗清谈,从不以世俗事挂齿。仲兄选善谈名理,似魏晋间人,尤嗜山水,尝绝大江,浮闽海。郑氏三兄弟最有可能回祖籍地探亲认宗者,只有郑选。
郑中有子兴祺、兴祉,生平不详。数传后有裔孙,名义配,慎于取与,言笑不苟,乡里称“正人”。义配生载军,载军生实生,均为太学生。其伯兄、仲兄后人情况,皆不清楚。
近期,福建龙台郑氏派人来浦口区寻找郑氏后人,他们只看见了浦口城的部分遗迹,而浦口城这一门龙台郑氏,连同黎家营的先祖坟茔皆已消逝于历史的尘烟中了。
(5)吴楫
嘉庆年间江浦人吴楫,其先祖也是军籍。吴楫《始祖吴公传》记述,其先祖吴玉,本为江西上饶人。元末以书生随明太祖转战有功,太祖即位,授玉平江水军督镇东南等处都指挥使(正二品衔),“念棠邑浦子口地当南北孔道,王室藩篱,遂家浦口”。建文初,靖难兵起,吴玉不肯与篡位者合作,朱棣心中有愧,仅削其官爵,其余不问。永乐三年(1405)追录太祖时扈驾之功,追封吴玉为横海卫右所百户(正六品),供职浦口,遂入籍于江浦。长子某世袭百户,其后嗣遂散居于今来安、凤阳一带,而次子则世居浦口城,子孙繁衍,至吴楫,为其第十四代裔孙也。若论吴楫籍贯,则真是一言难尽,若简单说,吴楫,江浦人。

(读书一生照片:江浦县城隍庙残壁,在城隍巷里)
8.处理军地矛盾问题
明代卫所大多驻扎于城镇、交通枢纽,又鼓励军户家属迁来同住,这些地方原本就不少土著居民,且大量军屯混杂于民田之间,这就导致许多军地(军民)矛盾。明代江浦县内当然也有这类问题。只是历史文献匮乏,至今尚缺少有关论述。
从明代姚宗仪《常熟县私志》卷六读到《何钫传》:“何钫,字子宣,号左泉……升南京锦衣卫经历。江淮卫,京卫也,而寄设江浦县,营房民舍址错相争,县令余乾贞、职方郎刘学朱各意偏护,为言官劾去,大司马潘季驯属钫,钫按兵部方策,不旬日息百年之争。”这段材料说的是江淮卫营房与民房占地矛盾。如前所述,江淮卫署驻江浦县城,因为负责南京水上运输,因此大量的营房在城南(今上河街、下河街)一带,西南郊长江圩区里有其大量的屯田,地皮纠纷在所难免。县令当然偏袒民利,职方郎(兵部官员)当然须保护军方利益,二人为此皆丢了官职,常熟人何钫(时任锦衣卫经历)受南京兵部尚书委托,很快解决此项“百年之争”。只是不知道解决方案究竟如何。
当时县令余乾贞是一个能吏,江浦县城就是由他主持建造的。《江浦埤乘》卷十九有《余乾贞传》,对此“占地纠纷”及其解决过程,记述稍异,细节更丰富。余乾贞,字秉智,号四山,浙江遂安人,隆庆二年(1568)进士,万历八年(1580)由监察御史获罪左迁为江浦县令。“时县民与江淮卫卒不相能,乾贞曰:‘比闾、伍,两皆吾人也,奚以町畦为?’宣布天子德意,与其帅约毋相犯,犯者互绳之。未几,兵氓和。”
不相能,就是互相不买账,余县令刚柔并济,晓以“军民皆我朝廷之人”之理,约以军民毋得相犯,犯则军地两方皆有权“绳之”。因此这一纠结许多年的矛盾才迅速解决。
万历八年(1580)新造江浦县城,也深深触及军地利害。据《江浦埤乘》等记载,余乾贞前任沈孟化议筑县城,先已“纲纪规画,条列便宜,上之大宪(应天府),闻之于朝,皆报‘可’。”沈县令的“规画”里当然包括筑城费用军地两摊、城墙军地分段修筑、施行“承包责任制”等等。《江浦埤乘》引用右副都御史,提督操江何宽《建旷口山城记》谓:“县与江淮卫错置,城成则兵民两利,故计工费,卫率减县什之四。江淮城迤北及卫南二面,县筑东西南三面,亦率多卫什之四。”就是说,江浦县与江淮卫合力筑城,县府筑东、西、南城,军卫筑北城及部分南城,费用及工程量,县、卫大体按六四开摊派。结果仅用时七个月,筑城工竣。这一成绩,既因为沈孟化等规划精细,也因为余乾贞施工组织得力,更因为军地矛盾处理及时。
结语:
除了上述八项,明代大量驻军,对明清时期江浦县居民成份构成、生产以及生活方式、民俗文化特征等方面,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,这些影响可谓至深至远,恐怕至今仍能找到许多痕迹。
2025年8月5日
声明: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,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。



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